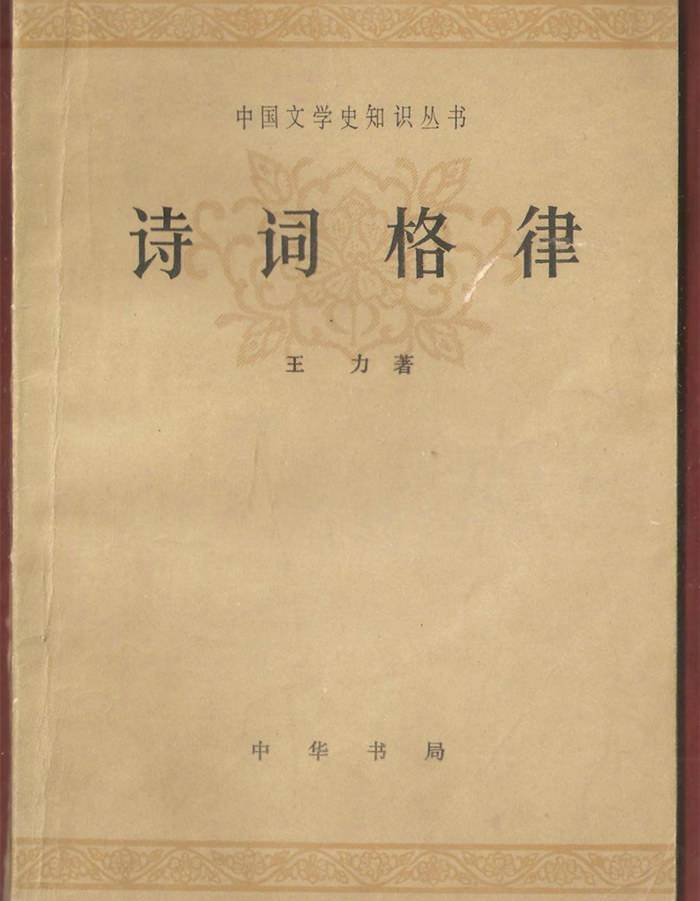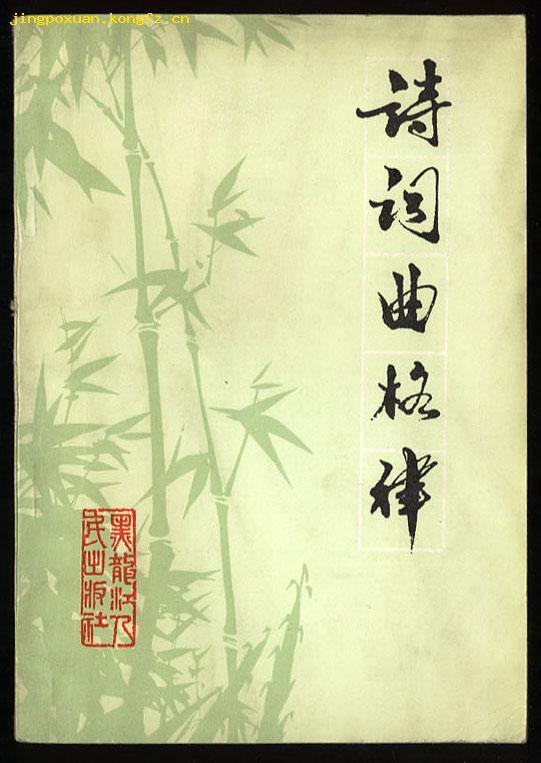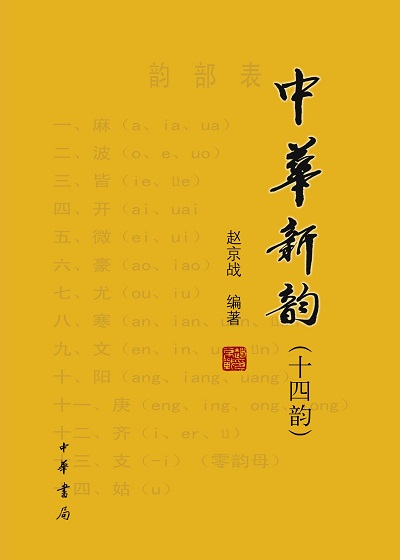《沧浪诗话》古诗理论

《沧浪诗话》是严羽所著的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,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、淳祐间。它的系统性、理论性较强,是宋代最负盛名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。全书分为《诗辨》《诗体》《诗法》《诗评》《考证》等五册。
诗辩
禅家者流,乘有小大,宗有南北,道有邪正。学者须从最上乘,具正法眼,悟第一义。若小乘禅,声闻、辟支果,皆非正也。论诗如论禅,汉魏晋与盛唐之诗,则第一义也。大历以还之诗,则小乘禅也,已落第二义矣。晚唐之诗,则声闻、辟支果也。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,临济下也。学大历以还之诗者,曹洞下也。大抵禅道惟在妙悟,诗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,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,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为当行,乃为本色。然悟有浅深,有分限,有透彻之悟,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汉魏尚矣,不假悟也。谢灵运至盛唐诸公,透彻之悟也;他虽有悟者,皆非第一义也。我评之非僣也,辩之非妄也,天下有可废之人,无可废之言。诗道如是也。若以为不然,则是见诗之不广,参诗之不熟耳。试取汉、魏之诗而熟参之,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,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,次取沈、宋、王、杨、卢、骆、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,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,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,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,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,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,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,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。倘犹於此而无见焉,则是野狐外道蔽其真识,不可救药,终不悟也。夫学诗者以识为主,入门须正,立志须高;以汉、魏、晋、盛唐为师,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。若自退屈,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,由立志之不高也。行有未至,可加工力。路头一差,愈骛愈远,由入门之不正也。故曰,学其上仅得其中;学其中斯为下矣。又曰,见过于师,仅堪传授;见与师齐,减师半德也。工夫须从上做下,不可从下做上。先须熟读《楚辞》,朝夕讽咏,以为之本;及读《古诗十九首》、乐府四篇、李陵、苏武、汉、魏五言,皆须熟读,即以李、杜二集枕藉观之,如今人之治经,然后博取盛唐名家,酝酿胸中,久之自然悟入。虽学之不至,亦不失正路。此乃是从顶上做来,谓之向上一路,谓之直截根源,谓之顿门,谓之单刀直入也。
诗之法有五:曰体制,曰格力,曰气象,曰兴趣,曰音节。
诗之品有九:曰高,曰古,曰深、曰远,曰长,曰雄浑,曰飘逸,曰悲壮,曰凄婉。
其用工有三:曰起结,曰句法,曰字眼。
其大概有二:曰优游不迫,曰沉着痛快。
诗之极致有一,曰入神。诗而入神,至矣,尽矣,蔑以加矣,惟李杜得之,他人得之盖寡也。
夫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;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然非多读书,多穷理,则不能极其至,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。诗者,吟咏情性也,盛唐诸人,惟在兴趣;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,透彻玲珑,不可凑泊。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象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,遂以文字为诗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;夫岂不工,终非古人之诗也,盖於一唱三叹之音,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务使事,不问兴致,用字必有来历,押韵必有出处,读之反覆终篇,不知着到何处。其末流甚者,叫噪怒张,殊乖忠厚之风,殆以骂詈为诗。诗而至此,可谓一厄也。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?曰有之,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。国初之诗,尚沿袭唐人,王黄州学白乐天,杨文公、刘中山学李商隐,盛文肃学韦苏州,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,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。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,唐人之风变矣。山谷用工尤为深刻,其后法席盛行,海内称为江西宗派。近世赵紫芝、翁灵舒辈,独喜、贾岛、姚合之诗,稍稍复就清苦之风。江湖诗人多效其体,一时自谓之唐宗。不知秪入声闻、辟支之果,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?嗟乎!正法眼之无传久矣。唐诗之说未唱,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。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,则学者谓唐诗诚止於是耳,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!故余不自量度,辄定诗之宗旨,且借禅以为喻,推原汉魏以来,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,(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,谓古律之体备也。)虽获罪於世之君子,不辞也。